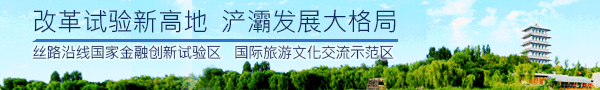那个支离破碎的夏天,却是我们唯一真实的乐园
作者:樊华 栏目:社会 来源:搜狐 发布时间:2017-07-02 14:34 阅读量:11871
原标题:那个支离破碎的夏天,却是我们唯一真实的乐园
前些天被朋友圈Liam要来的消息刷了屏,我当时在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声脏话。骂完了我就开始后悔——那声脏话让我显得好像对一些事仍有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似的。
一些事关于杨洲。09年失踪人口。
把绿洲介绍给我,是我唯一恨杨洲的事。就算没有他,早晚我也会爱上绿洲的,可他的失踪让这支乐队变成了我阴影的一部分。每次听到那些旋律,总会有种他还笑嘻嘻地坐在我身边的错觉。
认识杨洲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。那是07年的事,我如今仍然是一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,你就想想那时候得多屁吧。
但是,我和其他看《放羊的星星》、《转角遇到爱》的小屁孩又不太一样——那一年我离开老家去读大学,阴差阳错地接触了摇滚乐。
听摇滚的小屁孩自然就不能再叫小屁孩了,一般她们都自称为果儿,我也不例外,管他上不上乐手呢,先叫了再说。
很遗憾,我认识了杨洲,在这么傻逼的年纪里。
现在想想,他是怎么喜欢上那个天天自称妞儿,穿个粗高跟,画着歪歪扭扭眼线的傻姑娘的呢?当然,最开始见到杨洲的的也想不到,他会占据我生命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。
怎么说呢,作为一个刚当果儿没多久的小屁孩,我还是有些屁孩儿的陋习没有改掉——果儿们追求的是数量,追求的是范儿,我却还在追求颜值和真心。而杨洲既没有范也没有颜值,就算背了个吉他在酒吧里站着也还是格格不入,宛如一个来抓逃寝同学的辅导员。至于真心,就算我能确定他有,我也不敢确定我是否想要一颗辅导员的真心。
况且我认识他,是在五道口旁边的马路上。
那时候是冬天,我里面穿着骚浪贱小短裙,外面裹着一棉大衣,蹬着才会穿没多久的小高跟在刚下过雪的街上艰难跋涉。天也黑路也滑,眼看着前面有个人不知怎么摔倒了就没爬起来,走近了些才发现是个大爷。
那时候彭宇案没过去多久,人心惶惶的,加上天气不好晚上人又少,仅有的几个路人都回头看了几眼就走开了。
但我要声明,我没去扶大爷跟彭宇案没什么关系,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——那段路的积雪下藏着一大片冰,而穿着高跟鞋的我满脑子都是四个字:自身难保。
我一边艰难前行,一遍关注着大爷的情况,他似乎没有晕过去,不知道因为疼痛还是因为掉落在台阶下的拐杖,他好像只能坐在地上。我有些急,那天挺冷的,怕他就这样坐在地上冻坏了,可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没勇气脱了鞋在这样的地上走,只能边在心里骂着自己边努力加快移动的速度。
就在我马上要抵达大爷身旁,成为拯救他的天使时,突然被截胡了——“大爷你没事吧,摔哪了疼不疼,能不能站起来”一个穿着军绿色羽绒服的男生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,说时迟那时快边搀这大爷边白了我一眼:“愣着干嘛,过来搭把手啊。”
“哦,哦。”我边回应着边伸手去帮忙,可脚下一滑,伸出的双手改变了方向,拥抱起广袤的大地。最终,他明明一个人也很顺利地把大爷扶了起来,大爷一边感谢一边拒绝他要送自己到家的意图,两个人推脱半天,他终于目送大爷离去,想起我的存在。
似乎这时他才注意到我的高跟鞋,明白了刚刚我一系列智障般举动的缘由。检查过我的脚踝后,他叹了口气说还是背你去诊所吧。一路上他一会儿抱怨我怎么不早说自己不方便,一会儿抱怨大爷都没摔坏我身子骨也太弱了,我时不时回击一两句,不知怎么,竟一点没有初次见面的生疏。可能同为爱管闲事的人,有种莫名的吸引力吧。
后来具体再聊了什么我也记不太清了,似乎是从写病历时报的年龄开始,他得知了我在读他感兴趣的传播学,而他掏钱时掉落的拨片,让他透露了他业余时间组乐队的事。当时觉得是缘分,如今回过头来看,或许没有这些,有些故事也注定要发生的。
那时我也够傻的,好像什么都不在乎,什么也不考虑。直到他彻底失踪那天我才想起,他说他业余时间组乐队,我却连他的主业是什么都不知道,还有他的老家、他的学历,我甚至有种自己其实对他一无所知的错觉。
可我又总觉得,我对他比谁都了解。
我们常常待在一起一整天什么都不做,只听歌、看电影、弹琴、读书。或者说,我们仿佛只有这种相处模式。但就这样看着、听着、唱着别人的故事,偶尔插几句嘴,似乎也能直接走进彼此的心里。
我说过我唯一恨他的事是他把绿洲介绍给我,其实这也是我最感激他的事。是他让那个为了装逼听摇滚的女孩儿慢慢懂得了各种音乐的风格,懂得了怎样去欣赏、去体会。说到底,我恨的其实只是他的不告而别而已。
08年的暑假我跟家里说去做奥运志愿者,在他城中村的小房子里住了两个月。市民激情澎湃,我们百无聊赖。甚至最后我把为了装逼买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全部读完。那时读到普鲁斯特写的:“幸福的时光,即虚度的年华。”看看身边对着手机发呆的杨洲,我想也不过就是这样。
那一年迷笛的主题曲是逃跑计划的《08年我们结婚》,当时他们还没唱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火遍大江南北。估计不少爱摇滚的姑娘都对男友说过“到时候用这首歌跟我求婚吧”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
杨洲听到这句话时抓了一大把薯片堵住我的嘴:“想都别想,不可能。”过一会儿他看到我一脸的委屈和失落又忍不住笑出声来:“求婚也不能用这首啊,跟我混这么久,结果这么首歌儿就把你打发了,我那些艺术造诣白熏陶给你了?”
然后他拿起一把木吉他,唱起绿洲的《Stand by Me》。
记得那一年来了不少外国的大牌乐队,有夜愿、还有梦剧院,当然我们都没钱去听。不过我暗暗地开始存钱,希望以后绿洲来开演唱会时,不会因为财务问题失之交臂。那时候一起去看绿洲的演唱会变成我们最期待的事。
可是这个愿望在09年4月他们原计划在北京的演出取消后,再也再也不可能实现。
两个原因:大概8月末,我才得知绿洲解散的消息,事实上,七月就已经有这样的传闻出现,那时我却在忙着打听杨洲的下落。杨洲失踪了。
准确地说,不是失踪,而是人间蒸发,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我在他家门口坐了好几天堵住了房东,可她也不知道杨洲去了哪,房子里属于杨洲的东西也全都带走了;我去了我们常去的酒吧,没有人看见过他,有人说最近警方抓贩毒抓得很严,可我知道这跟杨洲的失踪没有半点关联;最后,我只能没事就去我们相遇的那条马路闲逛,我希望那个夜晚再次重演,只要能见到他,再摔多少次我都愿意。
当然,这些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有的朋友说我被骗了,有的朋友以为这些只是我的幻觉,有的人说或许他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,总有一天会再次出现。可我清楚知道这一切真真实实地发生过,却始终想不到他骗我的任何理由。而关于他会再次出现这件事,年复一年,我似乎也不抱什么期待了。
“Stand by me
与我为伴吧
nobody knows the way it's gonna be
尽管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如何”
后来再听到《Stand by Me》里最让我小路乱撞的这句时,再也找不到当时浪漫和甜蜜的感觉,只剩下对一语成谶的深深恐惧。
当得知Liam要来中国时,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。总觉得只要看绿洲的心愿没有实现,我和杨洲的故事就没有完结。
其实,可能我对找到他还是有点期待的,包括后来去音乐的相关行业工作,或许潜意识里,我总在期盼某天他会拎着吉他出现。至少跟我讲一讲究竟发生了什么,在那个支离破碎的夏天。
但时间越久我越忍不住质疑,何必呢?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一段:“远远看去优美而神秘的人和事,只要拉近了看,就会明白它们原来既不神秘又不优美。”或许我对杨洲的怀恋,只是对这段感情不知原因戛然而止的执念。
最近重新开始听《Don't Look Back in Anger》,他给我听的第一首绿洲。我想要放过自己了。
Liam的演唱会大概还是会去,不为了与他相遇,只希望或许能听到那句“don't look back in anger,at least not today(不要为往事而懊恼,至少今天别这样)”,然后与自己达成和解。
当然,如果你们也会去现场,还是麻烦帮我留意一下,他是否在你身旁。
男,30岁左右,寸头,爱穿黑色T恤。和别的男生最大的区别是,他的眼里有光芒。
文/十三妹丁无畏
郑重声明: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,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,与本站立场无关。仅供读者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社会摘选